程自迩:薪火长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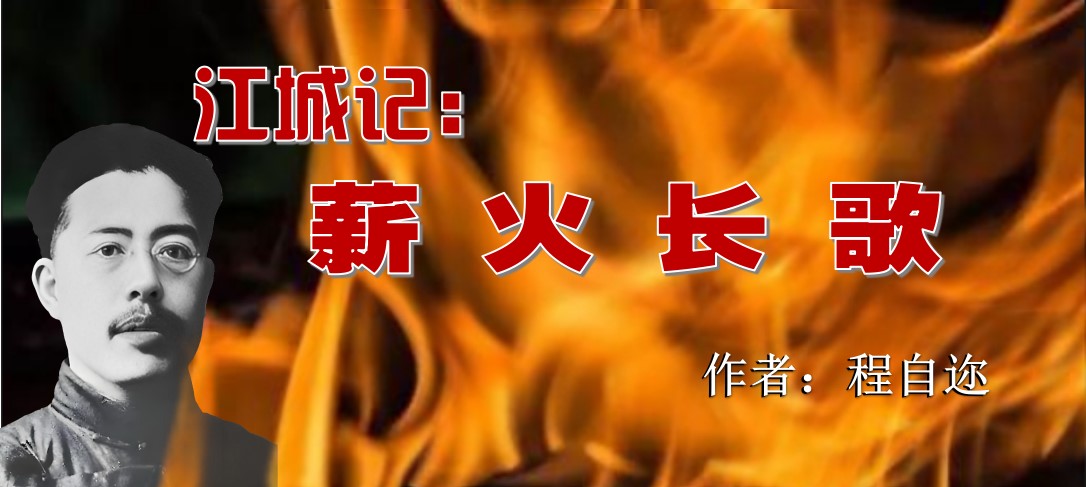
武汉的秋,是江水蒸腾起的雾,黏糊糊地裹着人。我攥着杯温热的咖啡,陷在公园咖啡厅外的软椅里。远处的摩天轮已然转过一圈,对面的咖啡还在等待它的主人。
面对狂敲回车键而不满的文稿,我的指尖划过键盘,敲击“钱亦石”却只搜出来零星字句。关掉屏幕,目光无处着落,溜进了绿荫深处——汉白玉石碑冰凉,历史尘封缄口不语。陈年的土腥气和凉意,无声无息地漫过来,心里头空落落的。
我在等待一个讲故事的人,更在等待一段有温度的故事。
1. 青 衫 志
恍惚间,汉口商业学堂阴影投下来,我的指尖触到门柱上“由义门”三字的刻痕时,风声骤然裹挟着黄包车铃灌入耳膜。再睁眼,湖广总督陈夔龙的车驾碾过积水,停在张之洞督建的新校舍前。这是1909年,20岁的钱亦石挤在新生队列里,青布长衫下摆沾着从家乡咸宁带来的红泥。“汉口之建商业学堂,旧已张文襄公督鄂之年创造经营。”陈夔龙的训词在细雨中飘荡。青年钱亦石的目光却黏在同学偷藏的《革命军》上,铅字灼得他掌心发烫。
1924年四月,武昌高师附小教导室里霉味刺鼻。漏雨的玻璃窗朦胧,钱亦石枯坐灯下。长衫袖口已磨出毛边——去年湖北一师学潮中,他因支持学生被教育厅革职。当局假惺惺递来复职函时,他当着厅长面将函件投入炭盆:“书案承不住破碎山河!”军警马蹄踏碎“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纸旗,糨糊混着血渍粘在青砖缝里,门轴吱呀惊破沉寂。中共武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董必武携着江风闯入,身后同为创建人的陈潭秋布鞋沾满胭脂路上的泥泞。董必武将《新青年》拍在案头,油墨味撞开满室潮湿,钱亦石指尖抚过封面:“笔锋亦可作剑锋。”陈潭秋指向窗外,蛇山轮廓在暮色中如伏虎,山脚下的黄鹤楼在战火中再次坍塌。钱亦石喉结滚动,油灯将他清瘦身影钉上斑驳砖墙:“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言撞碎在四月惊雷里,屋檐上雨水殷红如血。
钱亦石疾行在江城脉络中,1925年夏,执笔的《湖北目前最低纲领》在汉口生成里印发,二十一条主张如匕首划破阴霾:“肃清贪官污吏”“保障集会自由”。油印机在武昌黄土坡民居彻夜嗡鸣时,钱亦石的长衫袖口总沾着油墨——那是比学堂朱批更灼目的颜色。 1927年的汉口血雨腥风。钱亦石站在省党部礼堂,面对满堂惶惑的面孔剖析四一二政变:“须集中革命力量,打倒蒋介石!”话音未落,窗外传来警笛嘶鸣。他从容卷起讲稿,长衫下摆扫过满地传单,那身影穿过腥风,最终消隐在江汉关的钟声里。

红色教育家钱亦石
2. 挽 歌 情
踟蹰在昙华林的青砖廊下,1938年,这里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成立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主管抗战宣传工作。穿灰布军装的人们挟着油墨未干的传单奔忙不息,油印机轰鸣声里,那个眼眶通红的姑娘——钱韵玲,攥着刚取到的《钱亦石先生挽歌》谱纸,指节捏得发白。“您是钱先生的女儿吗,这曲子......节拍改过三稿”冼星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钱韵玲转身时,一滴泪砸在谱纸中央的休止符上,墨迹顿时洇开破碎。 她最深爱的父亲,为了理想里的那个中国,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永远留在了上海滩的寒夜里。与他并肩作战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在武汉阴雨绵绵的二月天里,与整座悲恸的城一同哀悼——哀悼一个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位永远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战士。窗外,署名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挽联“哲人其萎”在风中微微颤动,而第三厅的走廊上,时任厅长郭沫若正低声与时任宣传处处长田汉商议,如何将钱先生的遗志融入即将发起的抗战宣传周活动里。
自那日,街头巷尾的暮色总渗出一点温度。当冼星海攒足力量挥动指挥棒,歌咏团齐吼“到敌人后方去”时,总能在攒动的人头间寻见那双沉静眼眸。有次空袭警报撕破黄昏,众人奔入防空洞的拥挤中,他触到她冰凉的手腕,脱口而出:“令尊说歌声能震碎铁幕。”防空洞的阴影里,钱韵玲说起父亲弥留时念叨的武汉中学课铃。
七月流火漫过汉口的大智路,冼星海在油印室彻夜刻写新谱,这是他在武汉创作的第60个作品,身边的桌面上,铺满了这段时间的心血之作:《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大武汉》《歌八百壮士》……钱韵玲端着搪瓷缸进来,缸底沉着三颗暗红的枣,是她守在煤炉边煨的。他仰头饮尽,糖水淌过喉间——恰似那日她眼泪坠落的轨迹。窗外突然一阵喧嚣,报童举着“九江失守”号外狂奔而过。两人目光相撞,冼星海愤而将刻刀掷向蜡黄的谱纸。 战局在暗处扭转。十月寒风吹彻昙华林,第三厅墙上的“保卫大武汉”标语被敌机气浪撕开裂口。冼星海攥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电报穿过长廊,在堆满乐谱的储藏室找到钱韵玲。她正将父亲遗稿收进樟木箱,烧沸的理想在眼底突突跳动。钱韵玲指尖抚过电报纸粗糙的边缘,哼起《挽歌》里那句“你是黑夜的明灯”——此刻像冲锋号般铮铮作响……到延安去,到黄河畔去,两颗年轻的心从未有过如此的贴近。
车过江汉关钟楼,冼星海的目光掠过海海人潮,晨雾中飘来《松花江上》的曲调,钱韵玲轻轻和着调子,将一沓武汉歌咏团的花名册捂在胸口。卡车碾过满街破碎的《抗战画报》,径直向北驶去,把长江的呜咽谱成新曲的前奏,流向黄河,汇成更加磅礴的咆哮与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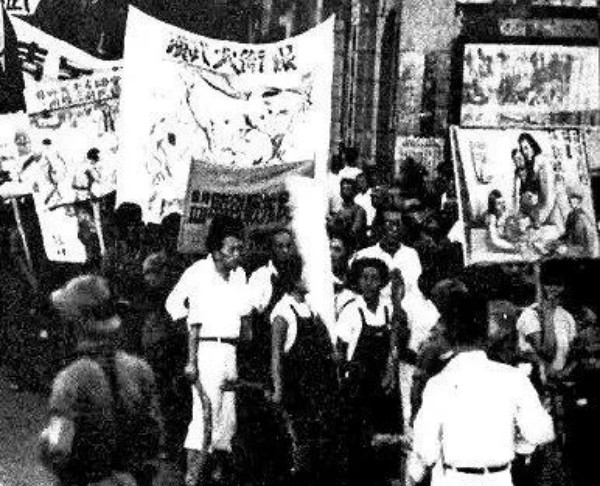
冼星海在武汉发动长江火炬歌咏大游行。

冼星海与钱韵玲。
3. 纸 弹 雨
第三厅的油印机昼夜嘶鸣,空气里弥漫着油墨与汗水的酸涩。钱远铎俯身清点传单,百万份《告日本国民书》《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堆成小山,油墨未干的日文字句在昏灯下泛着冷光——“侵略战争是人类的耻辱!”这些文章都是郭沫若亲手编写的。
“远铎,航空委员会的车到了!”同事的呼喊穿透雨幕。他直起腰,肋间旧伤针扎般刺痛。油布遮盖的卡车后厢里,整捆的传单浸染着墨香。他解开两捆,示范着将传单与小册子交叉叠放:“这样空投时才不会结块。”麻绳勒进掌心时,父亲钱亦石在他儿提时总说的那句话“没有国,哪有家”再次撞进脑海,此时距离父亲的离世不足四个月,作为钱家长子的他只能藏起悲伤,化愤怒为行动的力量。
车轮碾过积水的生成里。副驾驶座上,他紧按膝头一捆传单,纸页随颠簸簌簌作响。中山大道两侧,“同生共死,保卫武汉”的标语在雨水中朦胧,恰似他1935年与组织失联那夜,上海弄堂墙上被冲刷的联络暗号。当年父亲在亭子间低声告诫:“暂勿接转关系,每周回家汇报。”此刻他怀揣着没有党籍的身份,参加一项绝密行动——中国空军将飞越东海,在日本本土投掷传单,进行一场“纸弹轰炸”,钱远铎就是运送“纸弹”的一员。
卡车停在王家墩机场铁网外。哨兵刺刀闪着寒光:“证件!”钱远铎展开第三厅通行证,雨水迅速洇开印章的朱红。机库深处,两架马丁B-10轰炸机沉默列阵,这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轰炸机。地勤人员沉默地接过纸捆,雪片般的传单堆满机舱。一位飞行员肃然向他敬礼,皮手套上的机油蹭在传单边角,晕开一小片深蓝。 返程时雷暴骤临。卡车在汉口旧租界抛锚,钱远铎跳进齐膝积水中推车。暴雨抽打后背,他竟想起少年时随父亲在商务印书馆打包禁书的光景——那年他怀抱《共产党宣言》穿过巡捕密网,纸页的触感与刚刚怀中的传单如出一辙。
4. 少 年 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木楼梯上,钱远镜正对着穿衣镜整理青布军装,从内袋抽出抗大毕业照——背面新墨未干:“心里不惧死,只求死得值”。这是打算寄给姐姐钱韵玲的诀别书,墨迹里还沾着延安窑洞的黄土。他是钱家最小的儿子,在董必武的安排下参加了抗大第三期的学习,此刻回到武汉被分配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父亲已经离世,但去延安前,父亲留给他的字条被他珍藏在牛皮箱的最深处,每每展开,钱亦石那熟悉的瘦金体劈面而来:“胆要大,心要小,思想要坚定,耳目要聪明,态度要谦和,行动要机警。”六行箴言如子弹嵌入胸膛。三个月后,咸宁沦陷的硝烟熏黑了1938年的秋空。19岁的钱远镜毅然从武汉奔赴前方,率队攀上挂榜山主峰,将褪色的“国民抗日游击大队”战旗插进岩缝。山风卷起他破损的衣襟,露出腰间磨亮的驳壳枪——枪柄上深深刻着父亲叮嘱的首字“胆”。 霜夜,高赛岭的岩石冻如铁砧。钱远镜伏在隘口,左臂伤口渗出的血在麻布上凝成冰甲。“三辆铁王八,放近再打!”他沙哑下令。当日军卡车驶入死亡弯道,枪声骤起如爆豆。弹雨中他翻滚指挥,子弹擦过耳际时,父亲“心要小”的叮咛忽在耳边飘过。游击队员全身而退那刻,最凛冽的寒光在麻塘碉堡下迸射。钱远镜单人突前,血沫从敌人喉头喷溅,他瞥见岩缝里早开的杜鹃,红得像心头血,也像姐姐寄来的延安袖章。
1941年夏,樊口的江水裹着血腥气翻涌。钱远镜被缚在刑柱上,狼犬撕咬的剧痛中,听见江鸥啼鸣——当刺刀捅进胸膛,他最后看见的竟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那面穿衣镜,镜里少年正将军装纽扣系到领口,他高昂起头颅,闭上双眼,嘴角勾起希冀。父亲的信笺在晨光中飘落案头,墨迹叠着墨迹,烽火映着鲜血,如两代人相拥的骨骼,铸成山河间不折的脊梁。

钱远镜、钱韵玲、钱远铎(后排从左到右)与母亲王德训
我桌前的咖啡早已饮尽,杯底沉淀着苦涩的残渣。对面的那杯拿铁上,拉花凝结成一片苍白的霜花,始终未曾被动过。咖啡杯后坐着一位年轻女子,她有着与老照片里钱远镜如出一辙的圆润杏眼,眉宇间透着钱家人特有的英气。
她叫吴辰珵,一位从北京专程赶回武汉的电影导演。阳光透过婆娑的梧桐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钱远铎是我外公,”她的声音很轻,“钱韵玲是我姑婆,而钱远镜...... ”她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是我永远22岁的叔公。”昨天,我陪她站在九峰山烈士陵园的那方褐色大理石墓碑前,山风掠过松柏,她俯身放下的白玫瑰在风中轻轻颤动,像极了那个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的少年。 我合上笔记本,吴辰珵的泪水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她递来的老相册微微发烫,仿佛还带着1938年武汉办事处木楼梯间的温度——照片里,身着青布军装的钱远镜正对镜整理衣领,晨光为他镀上一层金边,照亮他衣襟下小心珍藏的抗大家书。那一刻,我终于读懂了他留在世间的最后字迹:“青年的生命已献予国家。”
凄厉的防空警报划破长空,每一年的10月25日我都会听到一次,今年将会是第19次。往昔我总不解其意,直到今日,才知道这声音与不远处这座白墙黛瓦的建筑之间共同书写着屈辱与抗争的故事——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而藏身于公园深处的武汉受降堂,四百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凝固着80年前那个永恒的下午:1945年9月18日,华中地区21万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部直三郎在此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俯首投降。
受降堂外,中山公园的百年古樟依旧亭亭如盖。老人们吊嗓的戏腔与孩童的欢笑声交织,摩天轮的彩灯在暮色中渐次亮起。八秩回响,受降堂门外的汉白玉石碑如同一个无声的历史坐标,从胜利穿越到盛世,沉静地诉说着我们民族的命运沧桑与浴火重生的荣光。
“他们究竟图什么?”采访结束前,吴辰珵带我来到了江边,她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轻轻抬手一指。夜色中,一艘货轮正逆流而上,汽笛声划破寂静,甲板上的集装箱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江面波光粼粼,像是冼星海当年在油灯下写就的音符,穿越时空,在这座英雄之城的水面上跳跃。
“你看,”她终于开口,“这条江永远向东,但总有人在逆流而行。”是啊,从钱亦石伏案疾书的深夜,到钱远镜血染长江的黎明;从冼星海谱写的每一个音符,到钱韵玲教唱的每一句歌词——这些逆着时代黑暗前行的身影,用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永恒的浪花。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牺牲,如同江底最坚硬的礁石,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清晰,为后来者指明前路。 逝者如斯,长江依旧奔流不息。我知道,那些消逝在岁月长河中的身影,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化作了两岸的青山,化作了江心的砥柱,永远守望着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作者与吴辰珵导演在九峰烈士陵园。

作者在钱远镜烈士纪念墙前。
(后记:2025年暑假,我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微电影《薪火长歌》剧组实习,结识了故事讲述人吴辰珵导演,并深度了解了她的家族故事。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时光长河中逆流而歌的灵魂。他们的故事,终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传唱。)
原载责任编辑:杜洵 朱曦东
注:本文为强国号首发 作者程自迩为厦门大学在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