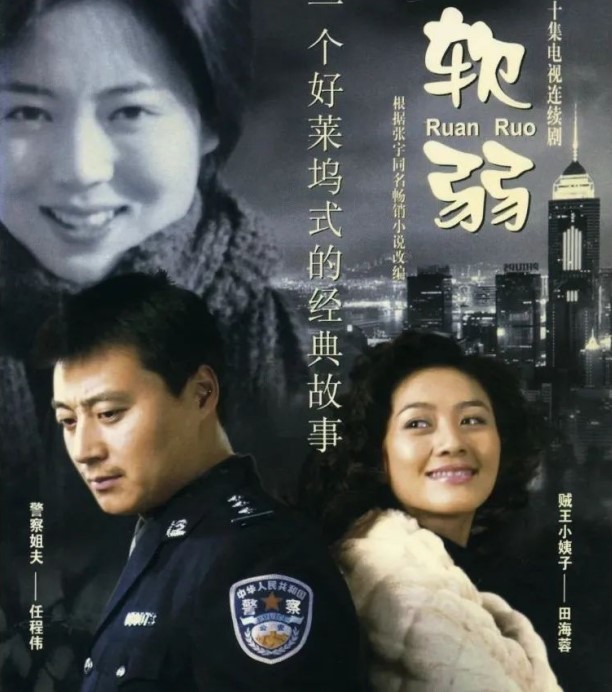张友文:论公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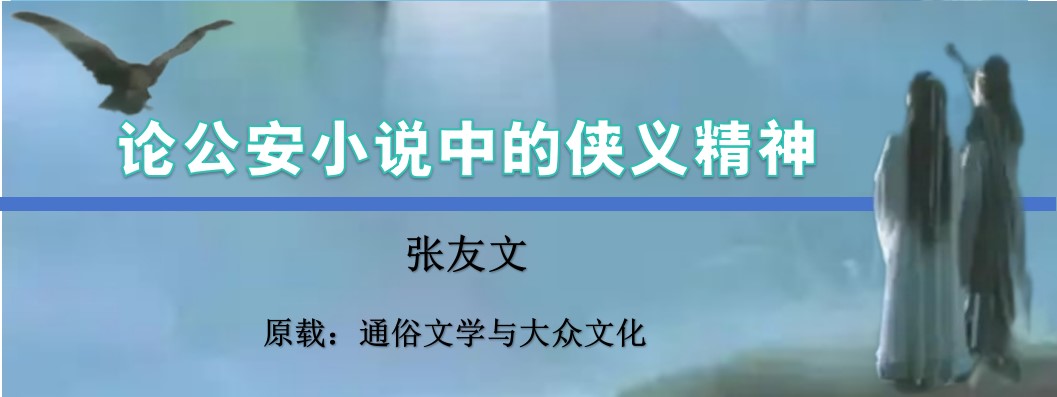
【按】公安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重要题材,从文脉渊源来看,公安小说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构成了内在的精神关联。侠义公案小说把侠客与清官“捆绑”在一起,让侠客与清官成为“为王前驱”的重要力量。“侠客+清官”的组合虽然拓宽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路数,却让侠客失去了“江湖”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武侠、言情、侦探等通俗小说被视为影响世道人心、破坏社会秩序的封建糟粕。而侦探小说改头换面后,又以反特小说的新面貌赢得了发展的机会。在反特小说中与特务展开斗争的国家安保人员,已经具备了公安小说中常见的人民警察的优秀品质。公安小说既书写人民警察的侦破工作与现实生活,也向读者展示人民警察身上的“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往往通过打击犯罪分子的刑侦故事来呈现。本文初刊《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感谢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副教授授权发表。
论公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张友文
摘要:侠文化一直以亚文化形态居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一隅,但它始终参与中国文化的建构和国民人格的塑造。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公安题材小说富含侠文化因子,其中的侠义精神与人民警察价值观吻合,人民警察价值观中的“公正”“为民”意识可以说与侠义精神一脉相承。发掘公安题材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旨在颂扬警察英雄,并提炼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
关键词:公安小说;侠义精神;精神密码
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迅速崛起,导致真诚贬值、道德滑坡、人心不古,甚至价值观出现紊乱。一些国人的是非、美丑尺度发生变化,他们崇尚实利主义和金钱拜物教,大力崇拜权力英雄和财富英雄,而对精神英雄却不屑一顾。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国家民族的强大不仅需要不断攀升的GDP,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保障,更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不断提升的文明,这是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得到普遍尊重的前提[1]。

公安小说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公安侦破类,以写警察侦破案件为主;另一类是公安非侦破类,以表现人民警察的生活为主。警察树立公正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客观要求。前者以“扫(打)黑除恶”故事居多,这些故事彰显的多是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人民警察面对黑恶势力不卑不亢,义字当先,“为国为民”,不受亲情、友情的羁绊,坚守正确的价值立场,公正执法。他们犹如侠义之士,把坚持正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侠文化本身固有的缺陷等复杂原因,侠文化一直以亚文化形态居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一隅。虽然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侠文化始终参与着中国文化的建构和国民人格的塑造,一旦遇到适宜的时代精神气候和现实生存土壤,沉潜于有识之士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处的侠文化精神质素就会被激发出来[2]288。侠无书,主要是一种民间文化精神[3]。
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二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4]学者陈夫龙把这段话提炼为“金庸把侠之精神提升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两面性,侠文化亦然。现在我们并非全盘接受侠文化,而是对它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使之真正成为新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实际上,侠文化因子也存于公安小说中。解读公安小说,发掘其间的侠义精神,就是为了寻访精神英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振国人的精气神,促进共同精神富裕。
一、“侠之大者”与“为国为民”
“侠”即一种重友谊、讲信义,助人为乐,舍己为人,刚强正直,伸张正义的气节品质;是一种人格上的自守与自持[5]。公安小说中的人民警察同样具有如此气节品质。司马迁之“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到黄侃之“苟强种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6],皆强调侠客赴汤蹈火、帮危扶困、拯世济难的功能。现实和公安小说中的人民警察在危难时刻也是冲锋在前,在生死关头也是赴汤蹈火。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侠义精神与公安小说中的警察精神找到了契合点。
侠具有三种文化形态:历史实存侠、文学形象侠和思想观念侠[2]23。思想观念侠则成为公道、正义和良知的象征。武和平的长篇小说《铸剑》[7]中的鲁沂蒙正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象征、英雄的象征”。小说第11章按照逻辑推理进行叙述应该是这样的:孙多余被当场击毙合情、合理、合法,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就此结案,毕竟这起报复行凶杀人案因果关系明显。但是痕迹专家在案发现场反复勘验后发现疑点重重:案发现场不止孙多余一个人的脚印,而且经过多次现场重建后断定孙多余进入张奇玉家之前,韩雨就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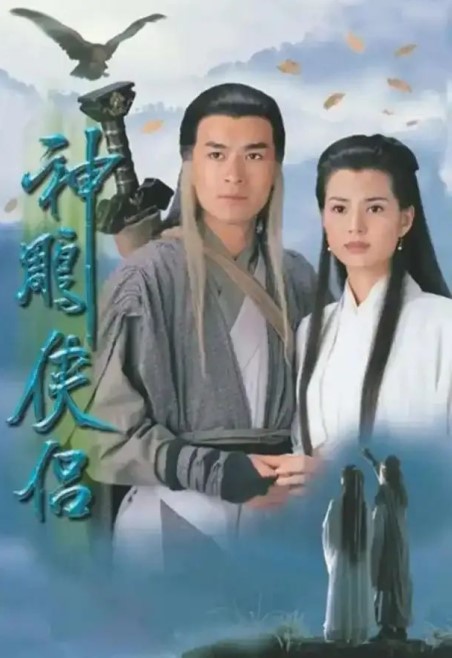
沂蒙的内心陷入从未有过的煎熬,若从个人得失,他真想快刀斩乱麻:韩、孙二人已死,向检察院提请侦查终结,不仅可以向市长交差,为朋友了难,又可以给社会一个说法和交代,使一切归于平静,各方皆大欢喜。当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从心底打了个冷战,绝对不可这样干,因为这不仅仅受良知的谴责,而且是对职业的不忠和背叛,生杀予夺,是非曲直,关乎公平正义,是横亘在内心不可逾越的底线。[7]293
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8]。作为警察的鲁沂蒙必须坚守职业良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他完全可以匆匆宣布结案,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不管外界压力有多大,他依然忠于法律、忠于良知、忠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忠于他人。原来鲁沂蒙也是“大侠”。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侠文化以永恒的存在价值和特有的文化魅力给有良知、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国人一种强烈的价值召唤,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家园、实现自我完善的思想资源[2]288。紫金陈的长篇小说《长夜难明》[9]中的侯贵平下乡支教时发现某高层性侵女学生的丑闻,立马向警方报案,结果被害身亡。他死后还被诬陷为强奸他人、畏罪自杀。身为检察官的江阳闻之义愤填膺,发誓为侯贵平讨回公道。为了追寻正义,他四处奔波,深入调查取证。他为此耗费长达10年之久的光阴,并付出了名声、前途、家庭等无数代价,连同自己的生命。
侯贵平案件的阻力重重,远远超过人们想象,因为有人隐藏真相,毁灭证据,知情者甚至被杀人灭口……号称“平康白雪”的刑侦副队长朱伟与江阳联手办理侯贵平冤死一案,结果沦为流浪汉,但他无怨无悔,他与江阳一样,心中也有永不磨灭的正义。
“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10]金庸笔下的大侠之所以活得很沉重,是因为他们身上承担的道义责任比一般人重得多。
他(江阳)一切行动都在框架内,既要对得起职业,又要对得起良心,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前途。
职业、良心、前途,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吗?[9]146、147
范渊凯在《明清侠义小说伦理精神研究》中说:“侠是具有独立人品和高尚品德的功力卓绝的人。”《长夜难明》中的江阳、朱伟等和《铸剑》中的鲁沂蒙都坚守做人的良知,其义举符合“侠”的诸多特征。“在新派武侠小说家,金庸、古龙等人的笔下,侠客精神已经成为对独立人格的坚持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譬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人虽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一致,甚至敢于抗衡整个社会的舆论,但是他们所追寻的是宁静和自由,而且在核心层面与民族大义是站在一边的。”[11]
由此可见,仅“为国为民”这一点就成为侠与人民警察的契合点。
张成功的长篇小说《黑洞》[12]中刑警支队长刘振汉面对友情、亲情的压力,排除万难,坚决依法查处龙腾集团。在刘振汉正式受理案件之前曾经犹豫过。而且,聂明宇的父亲聂大海还是他们家的大恩人;聂大海还是天都市市委副书记。在办案过程中,由于刘振汉得罪了一些权贵,他被停职,甚至被下狱。原来是市政法委书记陆伯龄以刑讯逼供致人死亡为由将刘振汉免职……借用庞天岳公安局局长的话来说:
这就是权势的威力,权大于法的现象一天不清除,类似的悲剧也就不会停止上演。你是人大代表,应该在人代会上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进行呼吁,依法治国不能老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12]572
公安局局长庞天岳良心犹存,正是他暗中支持刘振汉,才使得刘振汉的侠义精神显得更加耀眼夺目,才让一批与龙腾集团存在紧密利益纠葛的公职人员悉数落马。
刘振汉数起数落,几上几下:从刑警支队长这一职位贬到巡警队,甚至还站起了马路。等到他官复原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撤职,甚至沦为阶下囚。如果他没有“为国为民”情怀,他就不会遭受如此多的磨难。“自古英雄多磨难”,正是他凭借一身侠肝义胆才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之歌。
小说中的侠义与时代风云相结合最紧密、最突出者,便是为国牺牲的精神[13]。像刘振汉这样的警察都是除暴安良的侠客,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超强的本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侠义之举正好满足了读者潜在的“英雄梦”。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说,悉尼·胡克认为普通民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有三: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二是“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倾向”;三是“逃避责任”[14]。
公安小说中像警察刘振汉这样的侠客并不少,如李铭的短篇小说《血案》[15]中的警察不倒向当地党委、政府,也不偏向当地老百姓,而是站在中间立场,即把“义”放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其中包括“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公安小说中所蕴含的正义、良知和为国为民情怀正是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二、“公正”与“为民”意识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与“为民”意识也是侠义精神的体现。
郑保纯在《射雕的秘密》中指出“义”是侠客的社会属性[16]。“侠”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但是“义”这一核心层面不会变。“义是事之宜,即‘应该’”[17]。“应该”的标准是道德准则,按道德准则应该做的事不去做,便不具备勇敢的品格[18]。公安侦破类小说讲述的都是正义与邪恶进行厮杀和搏斗的故事,从而彰显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
在《侦探小说学》中:“侠义之士以义字当先,把坚持正义作为自己的作为准则。合乎正义,则舍生忘死地去干;违背正义,则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恩人主子,都义不容情地给以惩治。”[19]公安小说之所以耐读,除了其间故事情节吸引人、警察形象打动人之外,更主要还是因为有“义”这条线索贯穿始终。
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英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培根在《论法律》中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0]
孙明华中篇小说《人命关天》[21]中高文远局长给老局长尤建怀过生日的路上遇到张翠花,才知她并没有死。他立马把这一消息告诉尤局长。尤局长这才意识当年办错了案,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案。他马上邀约当年一同办案的现任代理县长程先锐去纪委说明问题,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案件,自己甚至险遭不测。尤局长在还道于当事人的过程中阻力重重,最终还是正义占了上风。
在梁羽生笔下侠士往往是正义、公道、智慧和力量的化身,他颂扬具有侠义精神的人,揭露和鞭挞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贪婪、腐败、暴虐和虚妄,从而体现出对民国武侠小说的承传和现代超越。梁羽生认为侠即正义的行为,也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22]。且看《长夜难明》中江阳的为人:
“怎么可能!”江阳冷笑着摇头,“绝对不可能,平反我自己的冤狱只是第一步,我根本不是为了我自己——”
吴主任手一摆,慢慢点头:“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为了把孙红运他们绳之以法。”[9]227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江阳倔强的抗争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公平正义。
古龙说“侠是伟大的同情”。“真正的大侠都具有巨大的爱心,这种爱心甚至推诸到他们的敌人身上。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3]公安小说中人民警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正是“侠”的角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中的“为民”意识则是“侠”的外化。贾文成长篇小说《煤殇》[24]中女警察给陆雯洁送衣服;范东峰长篇小说《风雨太平镇》[25]中的派出所所长李金玉对农村警察田超的关照;田耳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26]温暖人心之处是警察老黄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兑现一个承诺,即代替犯罪嫌疑人钢渣与小于一起守岁,于是他在大年除夕夜造访孤零零的聋哑人小于。
综上所述,公安小说中的情节或场景都彰显了人民警察的“为民”“公正”意识,颇具侠义精神。
三、“古侠”与“今侠”的区别
“侠客”就是豪爽倜傥、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乱世中他们或许反抗欺压、除暴安良、嫉恶如仇,凭借一身侠肝义胆与世间的一切昏庸与腐朽作斗争,不求显贵,不拜鬼神,剑之所指扫除人间不平事;在盛世时他们又或许能够成为匡扶人间正义的最快最利的一把刀,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27]。
“凭借一身侠肝义胆与世间的一切昏庸与腐朽作斗争”,在乱世中行得通,但是在法治社会却行不通。张宇长篇小说《软弱》[28]中反扒警察王海帮娜娜和春花私了案子即是。当地地痞流氓马三开口向娜娜发廊主顾要钱,娜娜和春花没有向警方报案,主要是害怕马三打击报复,她们不得已才向王海求助。王海替春花私了案子,可谓“见义勇为”,但是“作为警察,替别人私了案子,这是最忌讳的。”[28]125
《软弱》中王海出手完全是同情弱小,济危扶困。弱女子春花受无赖的敲诈,毫无办法,欲哭无泪,求告无门。她不敢向警方报案,害怕遭致打击报复。在万般无奈之下,她才向老顾客王海(王海经常在她那儿理发)求助。
《软弱》中王海分明就是“侠客”。春花为了答谢王海,欲以身相报。王海说: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你明白吗?我什么也不要你们的,我同样会为你们办事情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警察,警察就是干这个的。我既然答应你们了,我一定会认真去办的。[28]137
与王海类似的还有李铭的短篇小说《血案》[15]中的派出所所长毕记本,于怀岸的短篇小说《铁树要开花》[29]中的警察老麻。《血案》中的群众报案说荒土梁子村村主任郝大炮被人用镰刀砍倒了。毕所长与许小飞急忙赶到案发地,郝大炮对警察说德力用镰刀朝他行凶。而且,平日里德力就带着村民跟村委会作对。为此,郝大炮要求派出所严惩德力。毕所长对郝大炮说一定严惩凶手。当他带着德力回派出所的途中听了德力的讲述后,才知事情不是像郝大炮所说的那样,便让许小飞把德力的手铐给打开。还对德力说,有权利告郝大炮等人。
原来一身侠肝义胆的毕所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到了小说结尾,警察反倒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一并给揭露出来。
《铁树要开花》铁树想请村长龙习东帮忙提亲,因为龙习东是村长,面子大,又是他叔。可是,村长却拿着铁树送去让他帮忙提亲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子提亲。恼怒到极点的铁树这才起了杀心,砍伤了村长龙习东。为此,村长要求警察一定要严惩铁树,书记和乡长也打来电话说此事影响极为恶劣,要求派出所严肃查办。但是,警察老麻了解案情后不为某些人的指示所左右,只对铁树进行了15天的治安拘留处罚。
“在侠士身上,有一股超尘脱俗的洒脱之风,一股不为名缰利锁牢笼、不为私欲羁绊的崇高之风,一股舍己为人、视死如归的豪爽之风。”[19]170《软弱》所述故事发生在法制健全的当下,人民警察王海这个大“侠”的行为尽管合乎正义,却与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人民警察身份不符,其义举倒是与古“侠”匹配。“古书上说的‘侠’是‘以武犯禁’的人。意思是说,侠士往往超越和背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甚至不顾官府的阻挠和禁止,直接凭借自己的本领去抑恶扬善、铲恶除霸。”[16]165王海为弱者娜娜和春花伸张正义在当下法治社会行不通,毕竟他“超越和背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但是,他的义举值得肯定,因为是利他之举。
陈墨说:“儒家之侠的最大特点是关心国家大事及民族危亡,同时又愿意牺牲自我,鞠躬尽瘁。”[30]《软弱》中的娜娜和春花遭到马三欺负时,应该向当地警方报案,而不是向反扒警察王海求助,否则违反办案程序。在大力倡导法治思想的今天,警察的侠义精神虽然值得肯定,但是必须符合法律程序。
《软弱》中王海的搭档于富贵则是典型的“儒家之侠”。他面对妻妹刘莉的偷窃行为,并没有让儿女私情占上风,而是理性地对刘莉实施抓捕。这与王海帮扶弱者有所不同。李德裕《豪侠论》总结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31]王海虽然也是“正义感的体现”,但只能与“古侠”为类,而于富贵就是“今侠”。“今侠”在阳光下行事,他们不忘初心,不循私情,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在法治框架内执法办案,即坚守法治底线。不论是“古侠”还是“今侠”,其侠义精神中的利他、为民及为国等情怀与公安小说中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相吻合。
公安小说中的“人民警察”与历史上的“侠”有许多共同特征。解读公安小说,发掘其间所蕴含的侠义精神,是为了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小说正是通过建构人民警察形象,彰显道德力量、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吴丽艳,孟繁华.新文明的建构与长篇小说的整体转型[J].小说评论,2014(1):9.
[2] 陈夫龙.侠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3]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7。
[4]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M].香港:香港明窗出版社,1994.
[5] 曹萌,严萍.中国古代文学特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66.
[6] 释侠[N].民报,1907年第18号.
[7] 武和平.铸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8] 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18.
[9] 紫金陈.长夜难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
[10]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3.
[11] 范渊凯.明清侠义小说伦理精神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20.
[12] 张成功.黑洞[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13] 蔡爱国.清末民初侠义小说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85.
[14]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18.
[15] 李铭.血案[J].鸭绿江,2004(10):4-13.
[16] 郑保纯.射雕的秘密[M].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
[1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2.
[18] 倪乐雄.战争与文化传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59.
[19] 黄泽新,宋安娜.侦探小说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20]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21] 孙明华.人命关天血案[J].啄木鸟,2011(5):21-33.
[22] 汤哲声.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139.
[23] 汤哲声.边缘耀眼: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1.
[24] 贾文成.煤殇[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
[25] 范东峰.风雨太平镇[M].北京: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6]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1):68-89.
[27] 顾容毓.中国古典武侠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J].文学教育,2020(10):119.
[28] 张宇.软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9] 于怀岸.铁树要开花[J].青年文学,2007(10):68-73.
[30] 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6.
[31] 李德裕.豪侠论[M]//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