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传奇”的语用质疑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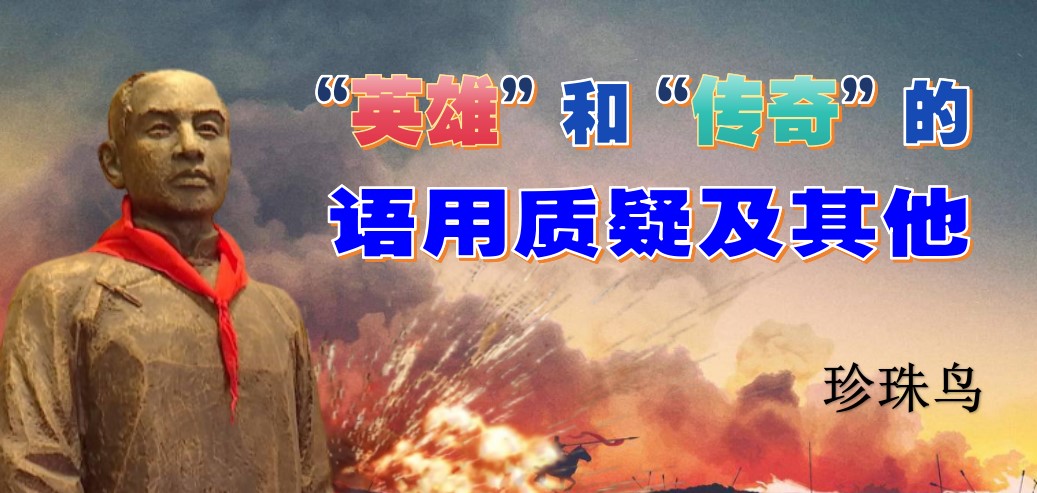
2025年8月间,在一个微信群里,我看到了由文先生撰写的《沔阳名人录》(书稿)之龙先生篇,其间《胡幼松传奇》的书名赫然映入眼帘,往事恰如泉涌,历历呈现眼前。
1976年夏天,我曾经奉沔阳县委宣传部金先鉴部长之命采写过《农民英雄胡幼松》一文,作为湖北省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会议资料,指定由文化馆擅长刻写的龙先生刻印成册。后来我专事教育工作,早已将这项经历置之度外。2009年,龙先生作为仙桃市(原沔阳县)文化馆的资深干部,将原作品名称《农民英雄胡幼松》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的操作,最终以《胡幼松传奇》为题成文发表,这一改动意味着与我的原创作品脱离了干系,但“传奇”一词所体现的传奇色彩给人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存在神奇性与传颂性,削弱了胡幼松事迹的历史真实性与严肃性,实乃败笔。胡幼松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潜江县委书记、潜江县与沔阳县南方接壤地段的农民运动领袖,在一次地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被叛徒出卖,落入还乡团之手,押解至潜江县城,被轧断双腿后用棺材钉将双手钉在门板上游街示众,昏死后一度复苏,仍然高唱《国际歌》,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彰显的是革命本色、英雄气概。胡幼松的英雄壮举本来是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存在,没有一丝半点的传闻和猎奇色彩。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故事抑或人物传记,应该尊重史实,还原历史,而不是拔高和粉饰,真实才具备亲和力、说服力与感召力。“传奇”一语的应用,提示文学性、修饰性色彩浓重,给读者带来的是超现实的联想和感受。浪漫主义往往会破坏作品本身应有的革命传统教育意义。试想,如果表现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将标题拟作《刘胡兰传奇》恰当吗?刘胡兰的事迹集中体现在她面对屠刀铁骨铮铮,面不改色心不跳,正义凛然。这不是“传奇”,而是历史的真实。如果标题使用“传奇”二字,就会先入为主,致使读者的猎奇心理油然而生,英雄的凛然大气由此得不到正面体现,反而黯淡失色,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意义也随之大打折扣。当然,关于唐伯虎的传记文学作品,题名《唐伯虎传奇》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只是读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具有极强的消闲性与娱乐性。其实,在《农民英雄胡幼松》一文的起草构思过程中,我也有过《胡大侠传奇》的闪念,甚至有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实空穿越联想,均觉不妥!胡幼松也是血肉之躯,是人不是神,他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正如他英勇就义前高唱的《国际歌》一样:“要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完全出于信仰的力量,不是什么超越现实的离奇现象!将《农民英雄胡幼松》题名改为《胡幼松传奇》,突出了传奇色彩,淡化了英雄本色,实在令人不解和痛心。倘若胡幼松同志在天有灵,他不会为这种“传奇”式光环感到骄傲,只会为此感到困惑和不安。作为《农民英雄胡幼松》一文的原创作者,我对这一改动的抵触情绪怦然爆发,溯及既往,心里确乎五味杂陈。
1975年,我在华师中文系学习。有个星期六晚上,学校在风雨球场放映露天电影。当时能看场电影都非常难得。室友陈勇搬起凳子,要求我陪他一起去看电影。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写点东西,脱口说了句“文艺界婆婆专政,就八个样板戏,看滥了,不看了”!当然,这句话当时只是用来不去看电影的托词,背后也确实表达了这样的潜台词:当时许多书籍都被列为毒草禁书,很多影片也被列为禁放名目,文艺创作凋敝不举,群众文化生活单薄乏味。后来被陈勇转告给了另一个与我带点个人恩怨情仇的同学范建,被范建向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告了密,指责我攻击“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妄图将我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在当时,攻击“文化革命旗手”是一个不小的罪名,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锒铛入狱的可能性都存在。我被工宣队驻中文系负责人陈师傅审查。幸好我是中文系大批判小组的学生成员,在“批林批孔”“评水浒”的活动中做出了有据可查、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批林批孔系列漫画被湖北省文化馆翻拍,在全省各地文化馆宣传橱窗里张贴发行。我创作的《投降派宋江》一书已由湖北省人民出版社审定通过,正式列入出版计划,并通报表扬了学院批林批孔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成绩显然,引起了学院与系领导的格外重视与支持。系里很多老师和领导出于保护意识纷纷出面为我说情。最终通过中文系党总支包括陈师傅在内的五位支委投票表决,以三比二的表决结果决定对我免于处分。但该决定还是在工宣队陈师傅的坚持下走程序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善写善画,在系里混的风生水起,但最终因为“攻击革命旗手”这桩糗事影响了毕业分配,发配回了沔阳,安排在沔阳师范学校。
1976年上半年,我参加筹办“沔阳县教育革命成果展览”,展览结束后,由于我有写写画画的禀赋,表现还不错,县领导觉得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比在教育部门工作更适合一些,于是县文化局与教育局商调,被教育局拒绝。当时党中央发动了“发扬革命传统,宣传英雄形象”的主题宣传活动,湖北省委宣传部与文化部门积极响应并进行了工作部署,沔阳县委宣传部经研究决定将陈场人民公社坡场大队胡幼松的英雄事迹整理成文,报送省委宣传部立项。这个写作任务指定由我来完成。我下坡场一个星期,前四天走访胡幼松家人与同村长老,召开了四场座谈会,后三天闭门写作,完成了两万余字的文稿,定名为《农民英雄胡幼松》。离开坡场大队之前,大队部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把《农民英雄胡幼松》文稿在会上进行宣读,特别对家庭出身、参加革命队伍、组织革命活动、惨遭被捕、英勇就义等相关情节进行了认真核实,经在场的胡幼松家人和同乡长老们落实认可并表示赞同后,才急匆匆回到县委宣传部复命。经县委宣传部金先鉴部长亲自审定,指定由文化馆善于刻印的龙先生刻写油印一百份,作为会议资料提交省委宣传部拟在黄冈(?)召开的相关会议审议。
县委宣传部的刘名汇老师告诉我,宣传部金部长决定下调令调人。通知人事局调档审查,那份关于对江青同志有不当言论但因“批林批孔评水浒”有杰出贡献、根据我党“给出路”的一贯政策、经系总支研究决定“免于处分”的决定书被曝光。对江青同志的文艺政策不满,显然不适宜在文化部门工作,调文化馆因此落空,反被下放基层,分配回了郑场中学。当然,这份档案材料并没有作为敌我矛盾定性,是必须为当事人严格保密的,我为什么调回郑场任教,其他人等并不知情,其间不乏胡乱猜想,认为我得罪了领导,或者能力有限。文化馆是有编制的,如果我进去了,意味着有人要出来。也有人把我视为事业上的竞争对手,搞了些恶意诋毁与排挤的小动作。我虽然很无奈,倒也有自知之明,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后来,“四人帮”倒台,在1981年的“清档”工作中,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这份“免于处分”的材料才得以从我的个人档案中被抽检出来销毁。没有了这份档案材料,我1982年调进武汉的事情才得以顺利通过。人生的路上纵然荆棘丛生,但我还是找到了破局的机会,打了一场人生的翻身仗。
因为《农民英雄胡幼松》的材料后被省里审议通过,坡场大队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始立项建设,胡幼松纪念堂、胡幼松纪念碑、胡幼松纪念广场相继落成。龙先生因誊印工作对材料比较熟悉,后续工作他的参与度日渐增加,并扩充至革命老区历史研究与地方志编修领域,可能补充了一些胡幼松事迹在民间传颂的“传奇”性情节,完成了《胡幼松传奇》这部新作。
当然,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我对自己所遭受的境遇逆来顺受、无怨无悔,不敢多吭一声。立足本职工作,也是小有成就,为郑场输出了一批可造之材。在表现胡幼松事迹方面,我只是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我离开县城后由谁来接替《农民英雄胡幼松》的后续完善工作也很正常。我调查走访加运思写作,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仓促成文,有所不足在所难免,需要进一步完善,完全在情理之中。说句实话,恢复高考后,作为高考把关教师,教学实践经验不足,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许多事情包括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全都无暇顾及,根本不可能对胡幼松事迹的进一步深层挖掘、整理完善再有关注。由谁把这项后续工作做得更好,我一定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大家都知道,那时的县政府部门,机械打字机都不多见,誊印材料多靠钢板蜡纸刻印,龙先生正因为能写一手漂亮的钢板字,才被调进文化馆工作的。而我在松滋县服役的时候,经常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参与了红红火火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典型材料”的采写工作与新闻报道活动,1972年就在荆州报发表了千字文《小评论不小》、在湖北日报发表了6000余字的大型人物通讯《克勤克俭的好支书(肖习勤)》,占据了湖北日报当日第二版的大半个版面。1975年还出版了《投降派宋江》一书。正是因为原松滋县县委书记黄真同志1972年调任沔阳县任县委书记一职,其夫人毛惠芳随调沔阳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对我比较了解,退伍回乡后,我才有机会在沔阳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当然,可能我的文字功力还不够成熟,但至少不会弱于当时并无多少写作实践与成就的龙先生。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说文化馆在组织刻印《农民英雄胡幼松》的时候,对文稿进行了修改,把我贬的一钱不值,经领导审定的文字稿件,怎么可能被随意修改呢?这是常识。当然,也包括了他对书名的全新理解与认识,他可能认为“英雄”之说过于朴实无华,不如用“传奇”更显神奇光鲜。对我个人的文字功底进行这样的变通和贬损,实在缺乏君子风度,大有落井下石之嫌。原创作品是在实际调查基础上整理成文的,是付出了劳动的。就算是你有所修改,你也不可能为了追求“传奇”色彩而脱离原创的事实基础,跳出原创的立意框架。对原创作者的劳动成果,你应该给出一个基本的尊重姿态!《胡幼松传奇》的书名反映的不仅是一个文品问题……。由于那个时期的社会法治建设不够完善,知识产权、著作权意识十分淡薄,发生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大可不必深究。
这段经历不仅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而且严重地挫伤到了我的情感生活。青年时期,我也有位心上人,也曾经有过频繁的通信往来。那时候写这样的信也不敢随意表露自己的懵懂情绪,怕对方理解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书信交谈中多的是什么“努力靠拢组织,积极要求进步”之类的话,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她倒是身体力行,入了党做了官,红极一时。我也遇到过赏识、爱护、着力培养过我的领导,总是找我谈心交心,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我摇头说自己不知道申请书该怎么写,他说那不成问题,我把别人写的申请书拿来让你抄上一遍不就行了。但我仍然婉拒了。因为我知道,入党是要审查档案的,弄得不好,抓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档案里的那份“免于处分决定书”又会再度曝光,说不定搞的我书都教不成,不是安排扫厕所就是安排去看门。自从档案袋里有了那个东西,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别说那样的女朋友我高攀不上,就算是言听计从,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她本来就是突击提拔的妇女干部,也被推荐选拔进医学院深造,那种高要求,高标准,高不可攀,我已经不适合她了,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她的前程,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一定会影响进一步的感情生活,与其今后要开家庭斗争会,不如就此淡出他的视野,结果当然是渐行渐远,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知是天安排,还是自然巧合,还有一位名叫小满的同学总在默默地帮助我,是她发现了我的长项,主动找到她熟悉的“大批判领导小组”的负责老师,把我引荐到中文系那个当时很出风头的“大批判小组”,我才有了充分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在“批林批孔评水浒”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做出了成绩,才能因此将功折“过”,免于处分。毕业分配以后,大家各在一方,各奔前程,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直到我从沔阳县调进武汉后,我们才得以重逢,并且同在一个事业圈里摸爬滚打,相互扶持成了家常便饭。此外,把我的言论向“工宣队”告密的那位范建也通过特殊途径夫妇双双调回武汉工作,小满和范建同在一个街区居住,平时走得很近。“四人帮”已经倒台,攻击江青同志已经不是什么过错了,所谓“工农兵学员”,本身是“文革”的产物,红色基因强大,极左思潮阴魂不散,有些人甚至利用一些学术环境唱红说M,尊孔崇儒,大放厥词诋毁改革开放。所以我还是很保守,觉得“免于处分”这件事说出来很晦气,不仅得不到我的“工农兵”校友们的同情,反而会引来他们的讥讽和嘲笑,甚至敌视,说得好听一点的会半褒半贬,说你“智商高、情商低”什么什么的;有的会立场鲜明,态度坚决,说你丧失阶级立场,思想落后,口无遮拦……。说东道西的都有,说出来只会惹来一身骚。直到退休,我怕影响到同学们之间的和睦相处,更怕自己孤立无援,一直没有把这段历史真相吐露出来。那位直接听我讲“文艺界婆婆专政”的陈勇同学因为肝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陈勇和我、小满、范建都是同班同学,小满心地善良,总想把我们几个约在一起去给陈勇上个坟,向他的家人表达一下慰问的心情。听说慰问的队伍里有我在,范建明确推诿不去,个中原委是什么,我与范建心照不宣,弄得出主意的这个小满一头雾水、一脸茫然。后来,因为范建是个烟鬼,终因肺癌上了奈何桥。再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出于感恩的心情,我才把这段历史讲给小满听了。她听后面带惊讶,反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把这事讲清楚?我的回答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面貌,讲清楚了,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划清界限”,跑八百里不回头……。话犹未了,面面相觑,大家的脸上都不约而同地泛过一丝苦笑。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作为熟人,我对龙先生在职业环境里的发展与个人成就深表钦佩。他是中共党员,积极靠拢组织,在领导面前,谨言慎行,适应能力比我强。对于一个坚守“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老实做事,低调做人”信念的人来说,他的这种能耐,别说这辈子,加上下辈子,我也学不到家,至少学不完全。“文革”时期是一个非常时期,亦称“十年动乱”,非常时期所发生的非常事态,实在不足挂齿。张志新因为一句大实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她比起来,我还算幸运的。时过境迁,我在这里并不是在为著作权问题耿耿于怀,而是在为自己“非常”时期的非常境遇长叹短吁。
呜呼,关于“英雄”和“传奇”的语用质疑,只是勾起一段回忆的切入口,更多的其实都是些题外话语……往事不堪回首。如今,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这块搁在心头的疙瘩因为时光的流逝,积怨被渐次稀释,早就烟消云散了。但愿我们都能保持健康,安度晚年。
